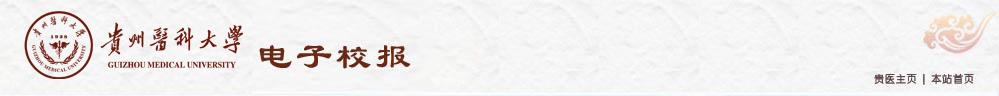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华北、华东进犯,祖国大片土地沦于敌手,各地流亡青年,纷纷奔赴西南诸省。当时贵阳成为大后方,众多的国内医卫界人士,亦汇聚于贵阳。在此时期,各战场及后方均需要大批卫生人员。同时来黔青年学生也需继续学习,故当时国民党教育部,便拟在贵阳新建一个医学教育基地,以应客观需求,遂有筹建贵阳医学院的决定。
文章题为《国立贵阳医学院创办记》,作者陈家骐先生。文章后面述及,贵阳医学院创建于1938年,陈家骐先生1945年时担任学院卫生课教职,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这篇文章可谓贵阳医学院校史的珍贵文献。
75年过去了,如今北京路的校园树木参天、花香鸟语,人文积淀颇厚;花溪校区亦楼宇林立,学子济济。1938年3月1日正式建校时,则因地制宜,客居他所,境况维艰。当时,学校办公和教学的地方分别在中山东路和阳明路。中山东路的王家烈公馆用以办公,而阳明路的两广会馆用以教学。建校当年的10月,为了方便学生实习,增设了门诊部。在门诊部的基础上,在两广会馆设立了附属医院,有小手术室一间。附属医院规模不大,只有40余张病床,与今天的贵医附院的规模自然不能相比,其设备也为多方募捐而来。抗战时的贵阳工业虽有所发展,但物资依然稀缺,多方募捐自是不得已而为之。艰苦中积淀的下来的精神,为学院的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建校之后,学生人数剧增,校舍自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1939年2月4日,日机袭击贵阳,制造了“二四”事件。此后,学校征得当时盐务局的同意,在六广门外空地上修建了19栋茅草房,之后又陆续修建了简易住宅8栋,以供师生教学和住宿之用。1940年,李宗恩院长接受了美国“洛氏基金会”赠送的2万美金,在南郊太慈桥划出百余亩土地,修建了一座两层教学楼,此后,又修建了一些宿舍,作为一部分学生的教学基地。1944年,日军入侵独山,准备进犯贵阳。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医学院北迁重庆,贵阳设立了留守处。这过程中,无论是设备还是人员,都有所损失。抗战胜利后,复又回迁贵阳。1950年,国立贵阳医学院更名为“贵阳医学院”,医学院从此翻开了新篇章。
建校之初,学院知名学者云集,比如内科学家张孝骞,生化学家汤佩松,传染病学家王季午等等。因抗战,他们不得已来到了祖国西南的贵阳;因抗战,在他们的支持之下,设立了这所医科高等院校。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读者幸。”就这些知名教授而言,抗战幸耶,不幸耶?对于贵州的医学卫生事业而言,抗战幸耶?不幸耶?
实际上,抗战时的贵州,西迁的名校很多,如: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广西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等;名家亦不少,如竺可桢、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等教授。尽管彼时物资奇缺,但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有一腔热血。时任国立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所作《国立湘雅医学院》一文云:
在当时的条件下,高等院校正常应有的科学研究是很困难的。虽然如此,在过去两年半中,学院尽量克服障碍,保持了科研的气氛和势头。例如:临床教师通过对某些贵阳地方病,如斑疹、疟疾、阿米巴痢疾等的调查研究;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学等部门也都分别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一个特殊的营养研究室正在着手筹建。所有这些工作都鼓励学生主动参加。由于缺乏基金,学院无力定期出版刊物,多数科学成果未能发表,甚为可惜。
《国立湘雅医学院》一文为张孝骞先生在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后起草的一份报告,虽然其中只说了湘雅医学院在国难之时的状况,但想必其他迁黔的高校及黔地高校的境况都应该相似,抗战胜利、振兴中华于此时此地既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克服困难的精神鼓舞。
以上算是对从史料中学习了贵阳医学院建校的历史。作为刚刚进入这座学府服务的我,了解这些历史尤为必须。不知历史,就无以知未来。历史蒙着尘土,但只要拂去尘土,就会光芒闪烁。我上高中之时,就十分向往贵阳医学院。无奈选学了文科,学科不恰,未能报考。大学毕业之后,方能有机会进入这一曾经向往的学府,成为其中的一员,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故在无意中看到陈家骐先生文章之际,也学习了贵医的创建历史,同时做了一回“文抄公”,加上题目为《贵阳医学院建校历史随记》云。
(作者系公共卫生学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