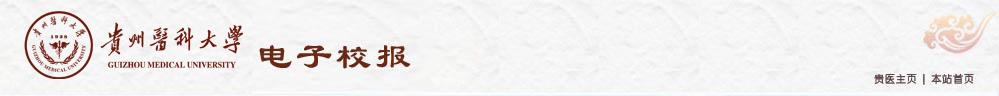小七孔之于荔波,似于兵马俑之于西安,长城之于北京。若说荔波旅游,这样标志性的景点都未曾领略,那这趟旅程总会给人或多或少的失落。我的荔波行,偏偏就是没有小七孔这一站啊!我的旅程,向来都是去不了最初想要到的地方。不过每次都会在失落中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就像荔波,并非只有小七孔。
6月8日,端午节,高考完第一天,买了下午4点左右到独山的票,收拾背包,带上我的大军壶,穿好鞋,戴上毡帽,出门。想到是端午节,在路上买一个红枣粽子。到了火车站,候车室里人山人海。在中国,只要是节假日,无论哪里的客运站,都是人海。在楼梯边坐着,听着歌慢慢等。不急,我有的是时间。
检了票上了火车,我想去独山,那里有很多抗战的遗迹。周围坐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估计是放假回家吧,毕竟是端午节。一路上,无话。等到饿了,我拿出粽子来吃。总是喜欢旅途中吃着这种有意味的食物,那会让我觉得,我并不仅仅是在坐着火车赶路,也在享受着这惬意的慢时光。近七点时,我到达了。下了火车后,坐公交到县里。在街角找了一家面馆,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味道不错,环境也不错。本来打算去深河桥的,但老板娘告诉我已经没有车去了,只好明早去。找了一家旅馆,比较旧了,估计营业时间比较久了,收费一般,应该比较安全,就住下来,放下包后,带上相机出门看看这座县城。独山,地处云贵高原,2013年贵州省第一座县级大学城落户独山县,为独山县大学城,位于该县城南部2公里处,我是从县城中心走路过去的,夜晚八点,一个人,只有公路两旁的灯光陪着我,那种独在异乡、佳节思亲的孤寂感异常浓烈。走着走着,感觉和花溪大学城很相似,一样的高校坐落,灯光璀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走到了这座县级大学城的东门,门口有许多夜宵店,人很多,生意都挺好的。好似中国学生都是爱吃,自然学校就是最不缺美食的地方。
这里的学校都没有放假,许多学生在操场上跑步。一束很强的橘黄色灯光照亮着整个操场,灯光下投影着他们颀长的身影。我站在操场迎接着灯光落在身上,那一瞬间我错以为身处学校,感觉整个世界都被这橘黄的灯光包裹着,温暖,旅途的疲惫都释放的干干净净。沿着跑道走了一圈,静静地享受着这异乡里不陌生的宁静。先前那种“异乡人”的孤寂随着黑夜消失在这橘黄色的灯光之中。哪怕还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去,我也甘之若饴。到旅馆时已经十点半了,洗漱完了直接睡了,只是一夜无好觉,整晚楼道里都有人上上下下,蚊子也多,一晚上就在半睡半醒之间过去了。
第二天下了很大的雨,在雨中等来了去深河桥的城乡公交,到了深河桥抗战胜利纪念园后,展览馆却是大门紧锁,似乎许久不对外开放了。我经过一段山路才到了深河桥,这座历史标志性的桥梁,在二战期间是西南铁路终点站。1944年12月初日本侵略军独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深河桥成为日军入侵步伐不可逾越的重要关锁之一。有史记载:八年抗战,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这座400多年的古桥,它历经太多太多的沧桑、见证太多太多的沉浮。这是由一颗颗石块一层层垒起的石拱桥。它是一座丰碑!在其旁的是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我们的英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他们的精神写照,他们的英灵与世长存。对于英雄,我无由来的钦佩,心怀天下,吐吞天地之志者,方为英雄。这样的大情怀、大格局,无由来的令人动容。
缅怀先烈后,搭了一辆摩托车到了兔场,即现名影山,这是西南巨儒——莫友芝的故乡。莫友芝与郑珍撰成《遵义府志》,史学界认为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齐名,梁启超称之为“天下笫一府志”,莫友芝与郑珍也因此声名大震,被人并称为“西南巨儒”。这位出生书香世家的人学巨匠,他的文学著作、书法造诣都让人望尘莫及。曾国藩曾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影山草堂是他幼时求学的地方,也是他定居金陵后为书屋所取的名字。很遗憾的是如今那里已是荒草丛生,寥无人迹。那里还有一座贵州省保留最完整的一所私塾——奎文阁,只是我没有时间再到荒山深处寻觅它了。这样极具文化价值的古迹不好好保护,却又劳民伤财的修建那些毫无价值的伪遗迹,真是现下中国之怪现象。
之后坐车赶到独山火车站,要坐火车去麻尾,再从麻尾坐车去荔波。在去荔波的途中会经过一片花海,名叫香草园,六月正值薰衣草盛开,在车上看着这片紫色花海,实在忍不住下车去当一次“采花贼”。走进紫色海洋后,你会觉得那是一条紫色的腰带,飘舞于青山间,绵延至青山尽头,真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游遍香草园后,在路旁等车,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打算今天就不去小七孔了,时间太紧了,六点景区就要赶人了,这点时间是无法好好领略小七孔的美的。然而,就是我这个想法,使得这次旅行与小七孔擦肩而过,想来我前世应该与小七孔有着五百次回眸吧。旅游,从来都是烧钱的,即使是穷游。
错过了最后一班到荔波的班车,我不得不为晚上的住宿考虑。此时一位黄色短发的妇女跟我说,他们家可以收我50元住一晚。原来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真的会给你打开一扇窗。那位大姐叫了一位老乡用摩托车送我到她家了。我喜欢摩托车,速度只是一个不太主要的原因。当我骑着它在路上飞驰时,我不仅能感受到清风拂面,头发向后飘舞,所有的景物从我的眼中滤过,我的眼睛没有一刻不是在享受着视觉盛宴。那是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无法做到的。那位大姐住在离香草园半公里的新街村,不一会就到了。我走进她家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迎了出来,带我到房间后,询问我吃什么,我点了一份在经济范围承受之内的西红柿炒鸡蛋。饭后想着出去走走,刚进村时就觉得这个小村庄挺美的,青山之下,悠悠稻田。刚出门就碰到一伙小孩,心想:免费的导游啊。询问他们愿不愿意带我逛逛他们的村庄,小家伙们和热情,争先恐后的在前面带路,然后,一拨人乌央乌央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最大的一个女孩在读四年级,很害羞,最小的一个才四岁,很可爱的小姑娘,很活泼,或许人都是越长大越孤单吧,慢慢接受着世界给他的认知,也慢慢失去自己的童真。跟着这些小孩一路蹦蹦跳跳的,好像回到小时候跟着一大帮玩伴去河里抓鱼,那是在我的故乡,每年夏天回家时,才走到半山腰就能看到山下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看到我爷爷奶奶的房子。那是属于我快乐的童年时光。
游完小山村后和小伙伴们分别,我回到旅店,那位大姐说答应我50元住店不是住在他们家,是住在他姐姐家。我想了想自己的价钱比起他们的房间来说的确低了一点,只有干净也没什么,就同意了。一会她就带我过去了,她姐姐家不是开旅馆的,只是让我借宿。比起旅店来说,我更喜欢这种借宿,住旅店只是利益,而借宿则带着人情味,这给许多羁旅他乡的游子带来丝丝暖意。那一晚,我睡得很香,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不停的传入我的耳朵,一夜无梦。
第三天清晨,被告知景区因为大雨已经停止售票了。抬头看着满天的乌云,觉得这次真是无法言说的旅行啊。店家送我到了镇上坐车,刚好赶上一班到荔波的车,我知道这次旅行里是不会有小七孔了,但是我在端午佳节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天公不作美就算了,可连荔波县城都没去看看,邓恩铭故居也没去参观,哪该有多不甘心啊!车一到站,我就打算直奔邓恩铭故居,时间真的很紧迫。可是走在荔波街头,看着街道两旁的椰子树,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风格,以及街道上的行人,脚步会不由自主的放慢,感受着这份异域他乡的民族风情。
县城不大,邓恩铭故居就在离汽车站不远的拐角的街道边上,可却不显喧闹、繁华,反而有种闹中取静的意味。参观是免门票的,还会赠送一份纪念卡,纪念馆不大,游客也不多,环境清雅,纪念馆后面是陈列室,讲述着邓恩铭的生平。我是从历史书中知道他的。当年,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中共一代最年轻的代表,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凝视着他的照片,想象着一位儒雅书生是如何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他曾在狱中写下一首诀别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他牺牲时不过31岁,正是踌躇满志的年纪、充满理想、少年英雄。不得不说,激起了我的热情,也曾幻想过,我若生存在民国,定是要像他一样为着自己的理想而献身。
出了邓恩铭故居,在城里逛了逛,就到汽车站买票到麻尾,刚好有一班车马上发车,一点没耽搁。一路上的风景很美,大雨冲刷过得世界很清澈,空气中还带着泥土的清香。吹着风,看着青山,就到了麻尾。火车来了,雨停了,乌云散了,阳光倾斜了一地,可我却要走了。
算了,留下一点遗憾也好,为了弥补,说不定我会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候再来一次。即便不来,那遗憾会让我记住独山、麻尾、荔波,记住一路上的风、雨、田野、村庄,而小七孔会在我的记忆中发酵,越来越浓,越来越美。
再见了,荔波。
(作者系2014级药学制剂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