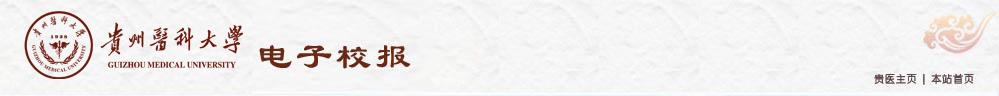踏遍青山捉跳蚤
跳蚤,只有芝麻粒儿那么小。它善蹦善跳,不易捕捉。李贵真研究跳蚤,可以用“呕心沥血”这四个字来形容。
跳蚤是一种寄生昆虫。它把人体和动物体当成“旅馆”和“饭店”。人身上有跳蚤,狗、猫、鼠、鸡、麻雀、燕子身上也有跳蚤。
为了捕捉各种各样的跳蚤,李贵真翻山越岭到贵州、云南的深山老林之中。这是一场有趣而紧张的战斗。
捕捉跳蚤,居然也要动用猎枪!当用猎枪刚刚打死野生动物,李贵真就赶紧跑过去,因为跳蚤都有这样的习性——一旦动物的尸体冷了以后,跳蚤就“树倒猢狲散”——纷纷搬家,蹦蹦跳跳离去。
李贵真把动物尸体放在白布上,细心寻找着躲藏在动物毛发间的跳蚤。跳蚤一见骚动,马上跳了起来,落在白布上,目标马上暴露了。李贵真立即用蘸了酒精或柯罗仿的棉花把跳蚤按住,跳蚤被麻醉了,老老实实躺在那里。李贵真小心翼翼地把跳蚤装在玻璃瓶或者紧口的小布袋里。李贵真眼明手快,能够将动物身上的跳蚤一网打尽。
李贵真拜猎人为师,还学会了挖陷阱捕捉活的动物。捉住之后,关在铁笼里,再把铁笼放在水盆上。这样,跳蚤一跳,便会跌落在水中。李贵真常常长时间守候在水盆旁边,抓住那一只只掉进水里的跳蚤,轻轻把跳蚤放入瓶中,生怕损坏跳蚤的半根毫毛!
有的时候,李贵真在山上抓住了野兽,干脆把它整个儿放进布袋,往袋里扔进蘸了酒精、乙醚、柯罗仿之类麻醉剂的棉花。没多久,野兽被麻醉了,野兽身上的跳蚤也被麻醉了。这时,李贵真把野兽放在白布上,用梳子轻轻梳,用毛刷轻轻刷,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决不放过一个跳蚤。
就这样,李贵真出没在密林兽群之中。有时,从一只野兽身上,抓住十几只或几十只跳蚤,那丰收的喜悦很快战胜了跋山涉水的疲劳。她不仅从野兔、野鸭、獐子、穿山甲身上找到跳蚤,甚至在一只猫头鹰身上抓住一只“雌性不等单蚤”,在一只雕身上发现一只“雌性犬栉首蚤”。李贵真认为,猫头鹰、雕身上的蚤,是因为它们常常捕食田鼠,跳蚤是从田鼠那里“搬”到它们身上居住了。
李贵真还发现,在野兽的洞穴里,常常有许多跳蚤。为了研究跳蚤,李贵真钻进野兽那又臭又脏的洞穴里,细心地捕捉跳蚤。有时,从一个洞穴中,竟能捕获几百只跳蚤。
李贵真制成一种“黏蚤纸”,把它铺在野兽的洞口附近,常能黏住不少跳蚤。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底,不知钩破了多少件衣服,不知被跳蚤咬了多少地方,李贵真没有叹一声气,相反,她觉得其中乐趣无穷。每当她从深山老林中归来,背回一大堆装着各种跳蚤的瓶子和小布袋,还没来得及歇歇脚,又投入另一场紧张的战斗。
跳蚤的“户籍警”
如果说捕捉跳蚤是一件非常细心的工作,那么,研究跳蚤则是一件比捕捉跳蚤还要细心十倍的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跳蚤就是跳蚤,都差不多;在跳蚤专家看来,跳蚤分好多好多种,并不一样。
李贵真开始研究中国跳蚤时,中国的蚤类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只有几个美国人在中国做过一点研究。李贵真决心建立中国自己的蚤类学。
要研究跳蚤,头一件事就是制作标本。下面是用文式语调,引述了制作一个跳蚤标本的复杂过程——并不是想请每一位读者读懂这种复杂的制作过程,而只是让你从中了解李贵真在研究跳蚤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采到跳蚤之后,先保存在浓度为70%的酒精里;
●用蒸馏水冲洗;
●放入10%的氢氧化钾溶液内,销蚀其组织,只留下角质部分,经过一至三天,使跳蚤变得透明;
●用蒸馏水洗两次
●放入醋酸溶液,约半小时至一小时;
●放入30%的酒精之中,约半小时至一小时;
●放入50%的酒精之中,约半小时至一小时;
●放入70%的酒精之中,约半小时至一小时;
●加入5%的甘油。一两天后,标本完全透明,可供鉴定之用;
●如果这种标本要长期保存,还要经过脱水、透明、制片等许多手续,最后用加拿大树胶封存,夹于两片玻璃之间。封存时,跳蚤的腿应当朝上。在左侧标签上注明宿主学名、采集地点、日期、采集者姓名。在右侧标签上注明跳蚤的学名及性别。
制作一个小小的跳蚤标本,竟然要花费这么多心血!
在制成标本之后,还要进行详细的鉴定。李贵真是跳蚤的“户籍警”,她熟悉各类跳蚤的特性,把它们分门别类。一旦发现一种新的跳蚤,就犹如化学家发现一种新的化学元素一样,激动得几天睡不好觉。
跳蚤的鉴定工作,比制成标本更为复杂。李贵真成天用显微镜观察跳蚤,然后在纸上一笔一画地画下跳蚤的形态图,画下跳蚤的眼、触角、气孔、臀板、爪、腿骨、锤骨、小颚、触须、梳齿……常常要花费几星期以至几个月的时间。
李贵真的研究工作,确如她自己所说,是一种非常平凡的工作。它是那么单调、枯燥,要求研究者非常细心而又富有耐心。李贵真是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发现了一种又一种中国的新跳蚤,使中国蚤类学这门空白的学问渐渐丰富起来。
1946年,李贵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一年,丈夫金大雄离开了她,来到北京,然后去美国留学。李贵真竭尽全力,支持他出国深造。这时,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儿子七岁,女儿一岁,小儿子刚满月。李贵真在贵阳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她居然不仅挑起照料三个孩子的重担,自己照旧开课,而且代替丈夫开课!她咬着牙,拼命地干。好在她自幼过惯了艰苦的生活,养成了坚韧的毅力。她能吃苦,常常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在研究跳蚤!就这样,在最艰苦的岁月中,她肩挑教学、科研、家务三副重担,仍接连发表许多关于跳蚤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被提升为教授。
跳蚤通信网
李贵真说过这样的话:“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研究跳蚤,只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我的工作,使蚤类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直到这时,我才认识到我的研究工作的意义。”
确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李贵真的研究工作不再是关在书斋之中,而是与祖国的脉搏紧紧相连。
李贵真还深深记得: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由于美帝在朝鲜发动细菌战,跳蚤成了美帝手中的杀人武器,李贵真怒火满腔,开始明白原来世界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家在研究跳蚤——我们研究跳蚤是为了救人,而帝国主义研究跳蚤是为了杀人!
为了战胜美帝的细菌战,各地都办起了短训班,纷纷邀请李贵真和金大雄去讲学。政府给他们夫妇拨了一辆专车,送他们到一个又一个地方去作报告,充分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那几个月里,李贵真夫妇可真忙得够呛!他们常常一大早就坐汽车出发,上午在一个地方讲课,下午在另一个地方作报告,晚上则召集当地科技人员开座谈会,了解当地跳蚤研究情况,深夜时他们在灯下把新情况补入讲稿,不断地进行修改……那时候,夫妇俩正处于科学上的“最佳年龄”——四十岁左右,他们以忘我的精神日夜工作。他们感到,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有意义。
由于各地不断来函索取讲稿,李贵真便把讲稿整理出版,写出了《跳蚤》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跳蚤的专著。
紧接着,李贵真又写出了一本十万字的《跳蚤概论》,这本书被认为是“我国蚤类研究工作的初步总结,是我国昆虫学、医学昆虫学、蚤传性疾病流行病学、医学界和卫生学界不可少的参考书”。它出版后,不仅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注意,也引起国际生物学界的注意,被认为是“关于中国蚤类学的权威性著作”,它的内容被许多外国学者所引用。有趣的是,这本《蚤类概念》渗透着爱情的力量:丈夫金大雄不仅帮助李贵真收集资料、讨论提纲,而且还亲自动笔为这本专著写了第一章绪论及第六章应用技术的最后两节。当年李贵真独挑重担支持金大雄出国深造,如今金大雄帮助她出科学专著,他们俩的爱情总是与科学交织在一起,是科学的爱情!
李贵真到各地去讲学,培养了许多新手。当她返回贵阳医学院之后,便不断地收到来自各地的信件。这些信件不谈别的,都是谈论跳蚤!新手们在研究跳蚤时遇上难题,立即写信向李贵真请教;新手们写出了关于跳蚤的论文,寄来请李贵真审阅;新手们找到了跳蚤新品种,寄来请李贵真鉴定……这样,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一个以李贵真为中心的关于跳蚤的通信网!
李贵真将这些关于跳蚤的通信,当做科学文献一样分类收藏起来。
李贵真对新手们的来信,每信必复。复一封信,常常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因为这些复信不是随手写下就完了的,而是需要经过查阅许多科学文献才能答复的。至于有的新手寄来跳蚤新品种,李贵真为了鉴定它,往往要花费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的时间。
为了共同研究跳蚤,李贵真通过通信,与全国各地的跳蚤研究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的朋友越来越多,她收到的信件也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信件是未见面的新朋友写来的。尽管每一封信都给李贵真增添了许多工作,但是她的内心充满喜悦,因为她深深感到,如今不是她单枪匹马在研究跳蚤,而是新秀辈出,后继有人。即使忙,也是忙得高兴哪!
李贵真是一个谦逊的人。不少青年人由于得到李贵真的指点,在研究跳蚤的工作中作出了贡献,当他们发表论文时,常常把李贵真的名字写在论文作者的第一个。李贵真见了,总是用红笔抹掉自己的名字。在她看来,帮助青年一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她甘愿当一颗铺路石子,让青年一代从她的身上踏过去,攀登蚤类学的高峰。
(未完待续)